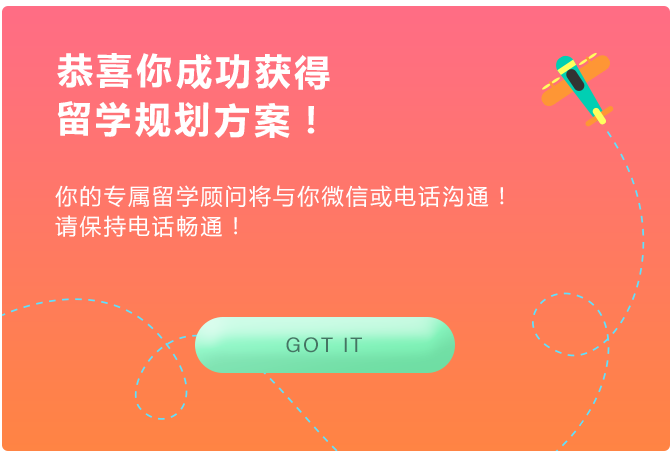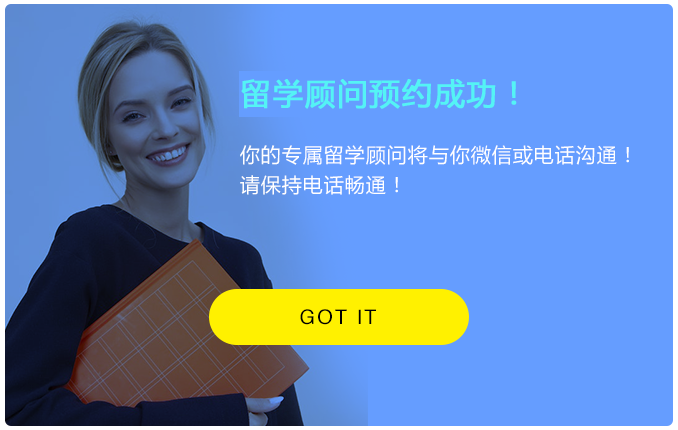東京都文京區(qū)目白臺,有一片被銀杏和櫸樹包圍的高臺,坡道盡頭矗立著一座磚紅色拱門,門楣上刻著“日本女子大學”六個字。1901 年,基督教信徒成瀨仁藏在這里敲響了日本正規(guī)女子高等教育的“第一聲上課鈴”;彼時,文部省尚未允許女性報考帝國大學,而他卻把“自の人格在り、使命を見て前進”寫進建校宣言,告訴 510 名首批女學生:讀書不是為了成為“更好的新娘”,而是為了成為“能照亮社會的自己”
。
一百二十余年過去,這句宣言仍在校園里回響。日本女子大學是日本唯一一所文理兼收的綜合性女子私立大學,五個學部像五片花瓣拱衛(wèi)著“女性教育”的核心——國際文化學部培養(yǎng)能講三種語言、跑遍四大洲的“翻譯官”;家政學部下設兒童、食物、居住三個方向,實驗室里既有 0~6 歲嬰幼兒觀察室,也有能精密到 0.1 ℃ 的味覺感官艙;2024 年新設的建筑學部更是日本女子大學史上的“硬核轉身”,學生在 1:1 足尺木構工房里搭梁架椽,用 BIM 模型把“女性視角的安心街區(qū)”寫進設計圖
。
“文理融合”不是口號,而是課程表上的強制代碼。文學部日本文學科的學生必須選修一門“統(tǒng)計入門”,理學部數(shù)理科學科的女生也要寫一篇“性別視角下的科學史”小論文。學校相信,只有當“感性”與“邏輯”在同一個大腦里相遇,才能孕育 21 世紀需要的復合型人才。為此,日本女子大學把課堂搬進東京都北區(qū)的食育支援中心,讓學生用數(shù)據(jù)可視化呈現(xiàn)獨居老人的飲食孤獨;也把人文學者請到微納米實驗室,討論如何在傳感器設計中融入“女性握力”與“手指弧長”
。
校園本身就是一座“女性史”的露天博物館。1898 年建成的成瀨紀念講堂,外墻仍保留著明治時期的半木骨架,內(nèi)部卻改裝成可舉辦沉浸式多媒體展的“柔性空間”;百年館高層 12 樓的“天空圖書館”,180° 玻璃幕墻外是富士山與摩天樓同框的景色,夜里 11 點仍燈火通明——學校與 Book & Bed Tokyo 合作,把沙發(fā)椅換成可平躺的“閱讀床”,女生們披著毯子寫論文,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經(jīng)典畫面。每年 4 月開學典禮,全校新生會走過一條由櫻花瓣鋪成的“粉色地毯”,把寫給自己的“十年后信”投進時光郵筒,十年后校慶時寄回——很多人第一次讀到當年的筆跡,才驚覺“成為自己”的種子早已在校園埋下
。
就業(yè)數(shù)據(jù)最能說明“種子”的發(fā)芽率。2023 屆 1180 名畢業(yè)生中, 89.7% 在畢業(yè)當年內(nèi)找到工作,遠超日本全國女性平均 78.4% 的水平;其中 212 人進入國家公務員序列,54 人考取大型商社,63 人繼續(xù)攻讀博士課程
。招聘季,東京證券交易所、聯(lián)合國開發(fā)計劃署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(fā)機構(JAXA)都會專門來校辦“女性專場說明會”,理由直白:日本女子大學的畢業(yè)生“既能用數(shù)據(jù)說服人,也能用故事打動人”。
國際化路徑同樣帶著“女大”特有的細膩。學校把“海外研修”拆成 7 天、21 天、一學期、一學年四種顆粒度:擔心安全的大一新生,可以先去首爾參加 1 周“女性與都市空間”工作坊;想挑戰(zhàn)學術邊界的四年級學生,則可以用“三明治”方式去英國愛丁堡大學做畢業(yè)研究,學分無縫轉回。對于外國留學生,日本女子大學提供“全日語授課”與“全英語授課”兩條畢業(yè)通道,2025 年在校留學生 261 人,來自 27 國,其中 73% 選擇用日語完成學業(yè),理由是“想體驗日本女性獨特的敬語與心境”
。
傍晚的目白臺,坡道下的超市亮起燈,女生們提著環(huán)保袋回宿舍,袋子里裝著今晚小廚房的食材:泰國室友的椰漿、北海道室友的南瓜、神奈川室友的味噌。她們把鍋碗搬到公共廚房,一邊等咖喱滾沸,一邊討論下周的“女性與氣候行動”路演。窗外,銀杏葉把路燈切成細碎的金色,像極了一百多年前那群不敢大聲說話、卻在筆記本上寫下“我要改變世界”的少女。日本女子大學之所以仍舊保持“女子”二字,并不是為了隔離世界,而是想讓每一個來到這里的女生,先在一個被理解、被鼓勵的空間里,確認自己“原本就可以”——然后再昂首走向更廣闊、也更復雜的天地
。
 日本
日本
 韓國
韓國
 英國
英國
 新加坡
新加坡
 馬來西亞
馬來西亞





 302
302
 2026-01-04 09:54
2026-01-04 09:54